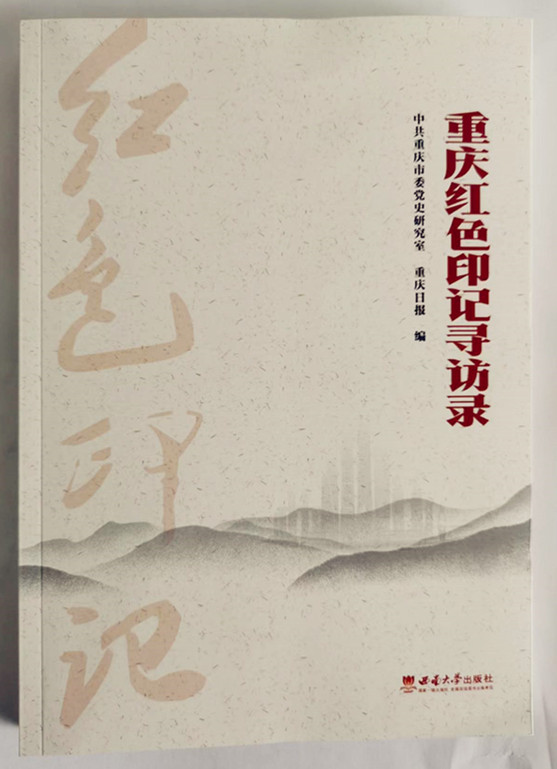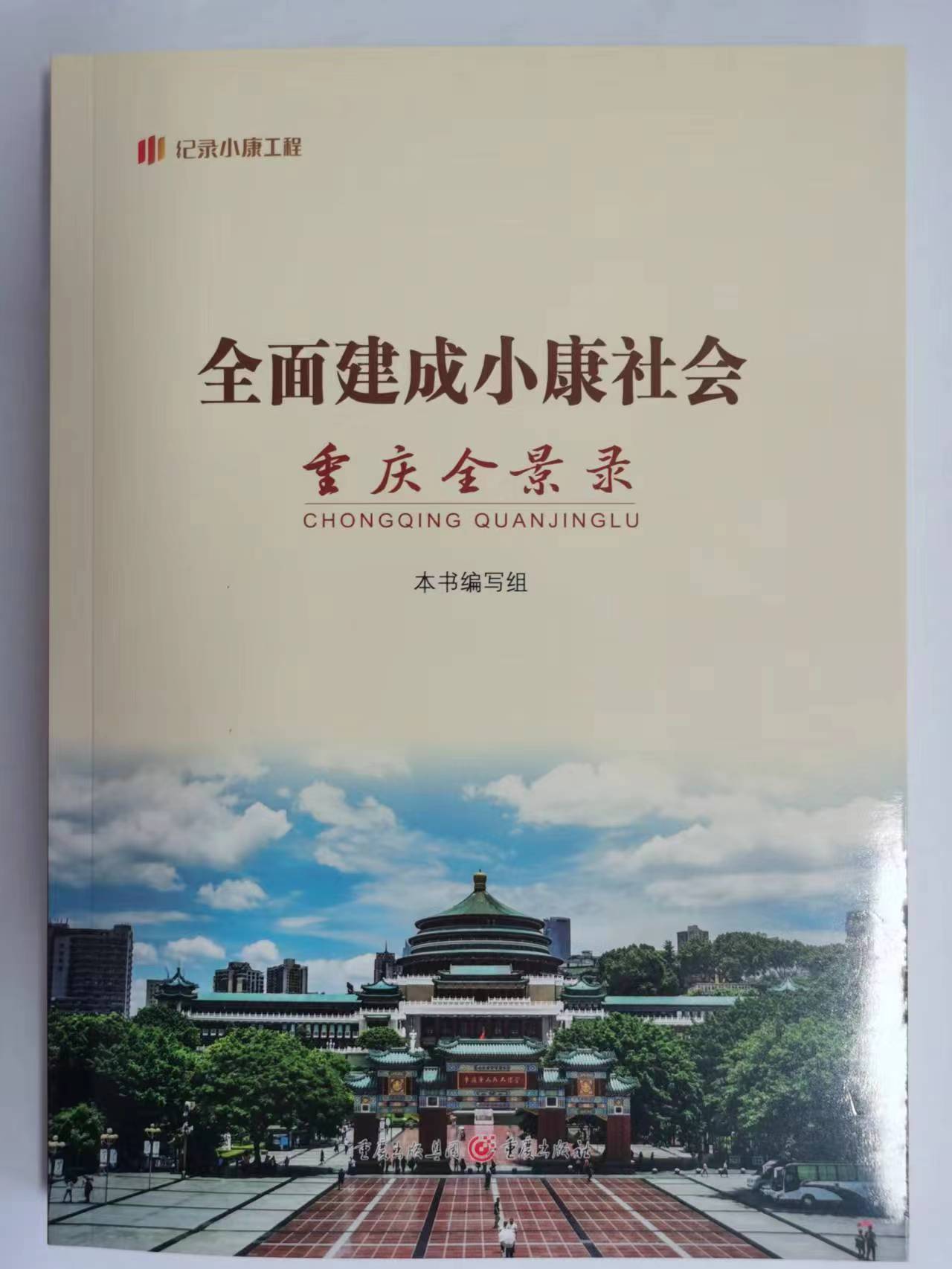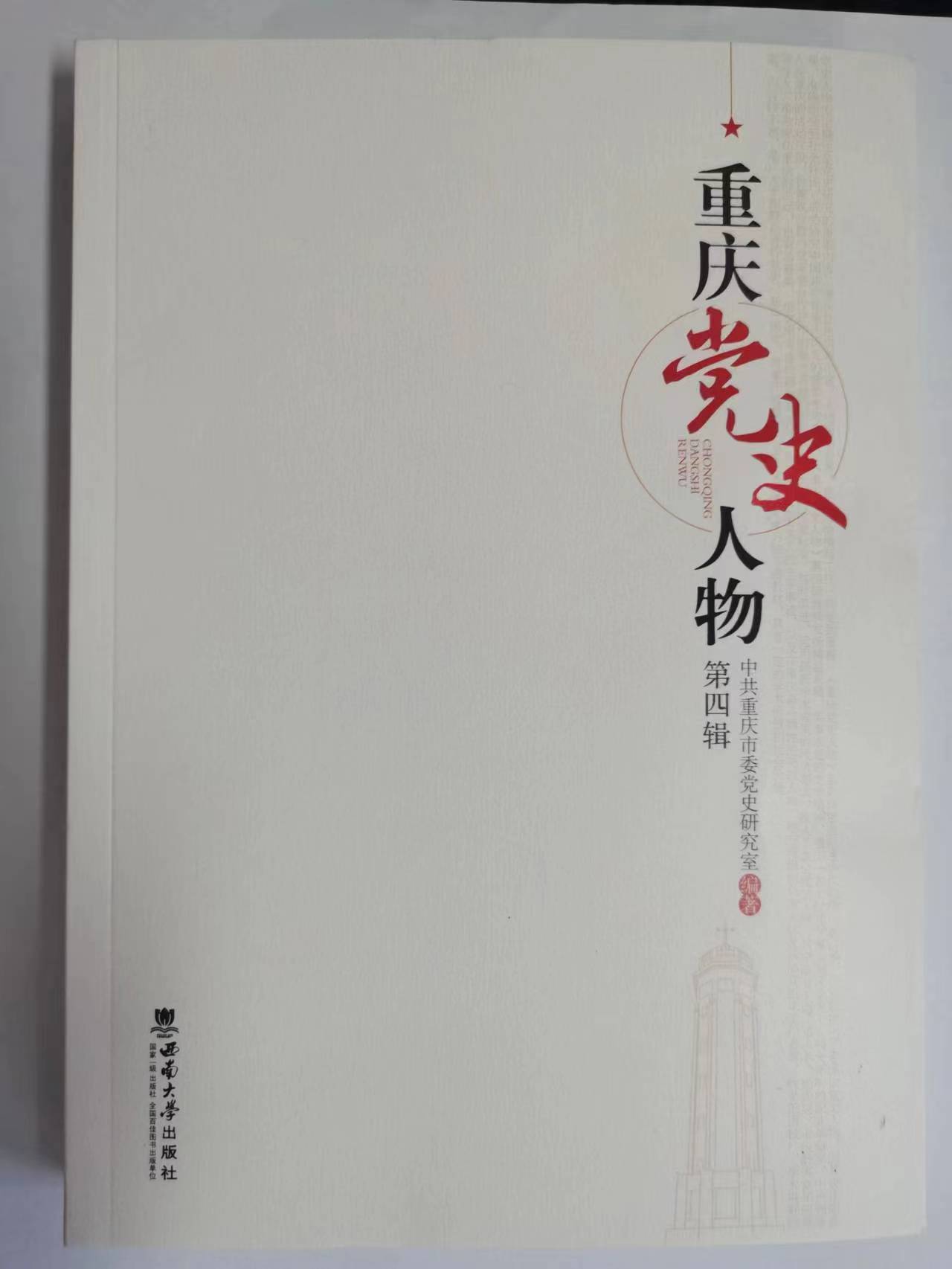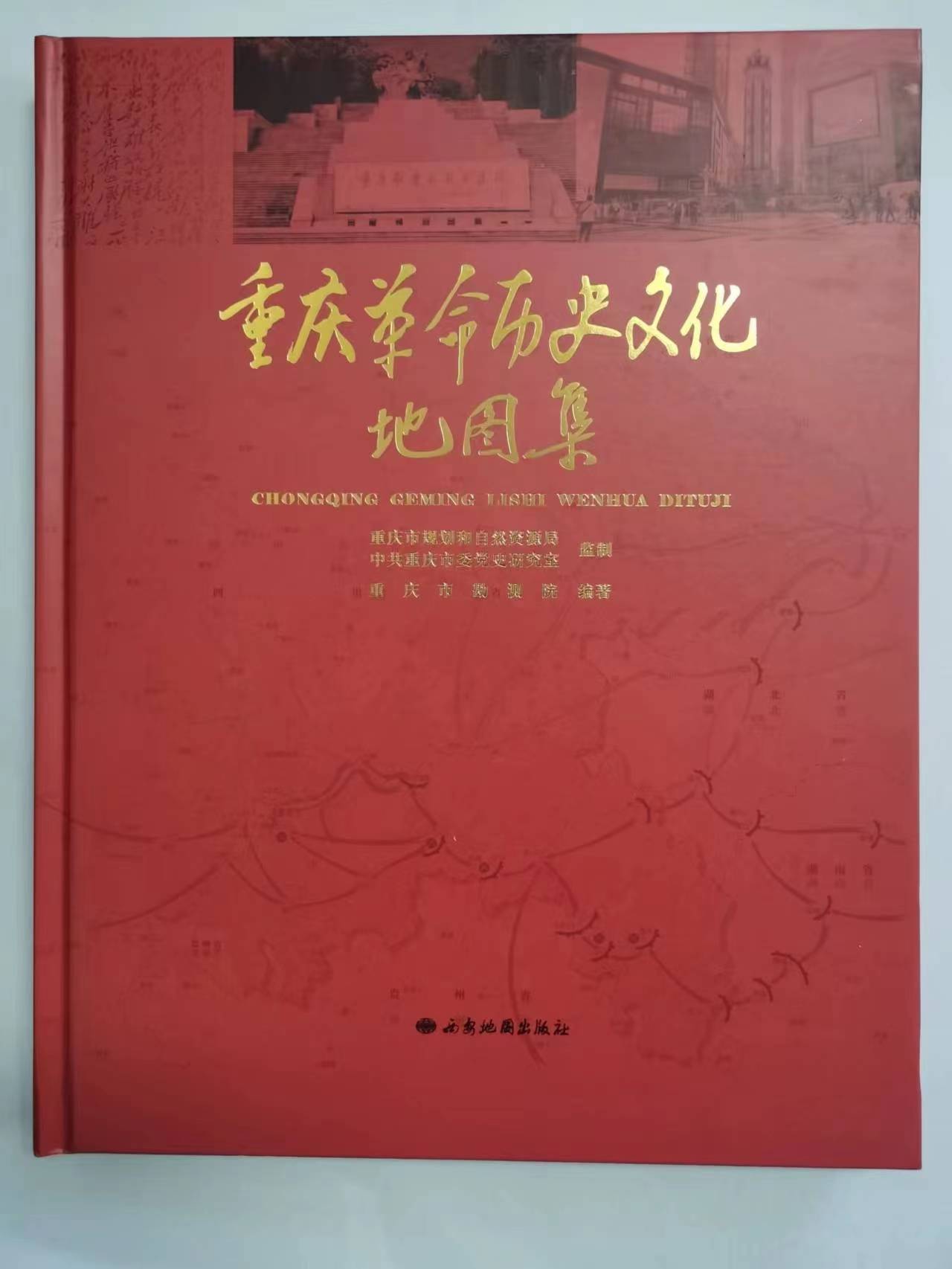吕岱
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职业?这或许是人生答卷中一个最普通的问题,相信每个人的回答都不尽相同。对于我国著名传染病学专家刘约翰来讲,他的回答异常简单:“是霍乱。”而这个“霍乱”的背后,却又包含着五味杂陈的人生故事。
学医心愿起于霍乱
1920年10月18日,一个男孩在浙江省宁波市孝闻街15号呱呱坠地,父亲为儿子取了一个让左邻右舍颇觉诧异的名字——刘约翰。
刘约翰的祖父母都是勤劳持家的人。祖父在孝闻街开了一个 小杂货店,外出进货由祖父亲自操劳,店里的日常买卖和盘账则由祖母一手打理。进了货,祖父还要挑着货担,走村串户吆喝着去卖咸菜,早出晚归,赚回几个铜板。一家人历经艰难,辛苦积攒,终于购房四五间,置地七八亩。
刘约翰的父亲刘贤良是独子,自小家里只让他读书识字,寄望将来能成大器,光宗耀祖。
宁波靠海,风气并不保守,且新风渐来,校有新学。刘贤良中学毕业后,经亲戚介绍,入读宁波华美医院附属浸会医学校。他跟着老师学习医学知识,问诊查房,进步很快,在十里八乡名声渐起。受浸会学校和外籍老师的影响,刘贤良打破了以字辈取名的传统家规,给儿子起名刘约翰,希望他今后跟自己一样学医,以虔诚之心服务社会。
刘约翰1935年7月至1938年6月在宁波浙东中学读高中,就在毕业那个夏天,宁波霍乱横行,其状触目惊心。民国时期,中国人的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非常差,卫生习惯也令人堪忧。别说宁波这样的地方,就是热闹繁华的上海,也不能幸免。曾经有一位法国人真实地记录了1843年上海开埠时的情景:“进入上海小镇,用扁担挑着敞开着的木桶的男子便迎面而来。他们是大粪搬运工,沿着固定的路线穿过城市。倘若跟随这些掏粪工,你会发现,他们走到附近的沟渠两侧,将木桶里的污物哗啦一声倒入敞舱驳船或另一种船舶里,污满为患时,船只便被牵引到乡间的稻田里。废物被胡乱倒进水中。沟渠之水少有流动,至少还不足以清除绿色淤泥,改变浑浊发黄、满是污秽的水质。可就在这条船旁边,人们正舀水来饮用和烧菜做饭咧。”
旧时江浙一带,湖泊众多,沟渠交错,以致传染病始起,传播甚是厉害。霍乱,被称为“最令人害怕、最引人注目的19世纪世界病”,也曾严重地一次次波及到中国。刘约翰亲眼见到附近乡村冒出不少新坟,也常见披麻戴孝、哀声不绝的送葬人群。道路之上,不乏行人突然栽倒再也起不来的惨景。那时,刘约翰所住的孝闻街到了闻霍乱色变的地步,有老者捂住鼻道:“古人云,挥霍之间,便致缭乱,真霍乱也。”
出于医德仁心,刘贤良不避“时疫霍乱”,在一座破庙里对乡亲们施以援手,积极救治,从不拒绝。
刘约翰陪伴父亲左右,最初见病人上吐下泻,有气无力,神态惊惶,年幼的他非常紧张。看到父亲镇定自若地忙上忙下,他“咚咚”直跳的心才平静下来。父亲需要搭把手时,他赶紧趋前,不避病人的呕吐秽物,打扫卫生,还学着指导病人与亲属怎样避免交叉感染。其时,他不明白父亲用什么药和什么方法救治病人,也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把他带在身边,但一颗悲天悯人的种子就在那时悄悄种下。许多年后,刘约翰在一份《自我鉴定》里朴素地写道:“当高中毕业时某年夏天,宁波发生霍乱大流行,家父在一庙宇内主持一时疫医师,创救病员,常带我去作伴。当时为医师的神圣任务所感,立志报考医学。”
可以说,是“霍乱” 使刘约翰选择了医生这个“神圣职业”。也可以说,在父亲的影响与熏陶下,他走上了治病救人的道路。
炮火中的学习岁月
1938年7月,在父亲的鼓励下,刘约翰考入上海医学院。但是,自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日军的铁蹄之下,中国大地没有一所学校放得下一张平静的课桌。
上海沦陷后,上海医学院师生开始分批内迁。1939年9月,高年级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从上海乘轮船途经香港到越南海防登陆,而后改乘滇越铁路前往云南。据当时的学生回忆,从越南平原进入云南崇山峻岭的那一刻,师生精神大振,全体起立,不停含泪高唱抗战歌曲《旗正飘飘》:“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在肩,刀在腰,热血似狂潮,好男儿报国在今朝……”随后,第一批师生迁到了昆明附近的白龙潭。刘约翰撤出上海较晚,他后来写道:“1941年,读完医三之后,学校内迁,先云南昆明白龙潭,又至重庆歌乐山。此后与家中失去联系。”
战争时期,重庆的生活异常艰苦。歌乐山上,虽有水田、水井和堰塘,但当地聚集了众多机构和学校,人太多,学校有时只能每天分给女学生一盆洗用水,男同学则要自己去找水。饭桌上,同学们吃的是掺有稗子和砂石的米饭。灯油更是不够,省着点也用不了多久,晚上也无法学习。学生睡不着的时候,晴朗之夜,只有远望星空。秋冬之际,常常大雾弥漫,伸手不见五指,眼前茫然一片。更恐怖的是,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在长达5年半的时间里,日本飞机对重庆展开“无差别轰炸”,无辜平民百姓吃尽苦头,整天提心吊胆。
日机侵袭时,刘约翰和同学们站在歌乐山上,看见山下城里硝烟四起,听到不绝于耳的警报声和轰炸声,一心想着早日学成,上前线救死扶伤。没有大雾的时候,他们一边远眺嘉陵江,一边一遍遍唱着由端木蕻良作词、贺绿汀作曲的《嘉陵江上》:“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在嘉陵江和长江的下游地区,则是刘约翰的家乡,触景生情,他倍思亲人,担心父母的安危。
1944年6月,刘约翰从上海医学院毕业。7月,被位于重庆高滩岩的中央医院聘为内科住院医师,直到抗战胜利,才随医院返回上海。1948年,他与同是医生的胡景楣在上海喜结良缘,婚后,陆续有3个孩子来到这个家庭。
炮火中求学的经历,无疑是莫大的鞭策,使刘约翰更加珍惜学习,也更加珍惜生命。
血防战线送瘟神
从医生涯中,刘约翰在血防战线取得的成绩无疑是重要的一页。可是看他的简历和自述,却写得极其简单,我们只能在蛛丝马迹中寻找线索。在一份简历中,有这么一行文字:“1950年1—4月参加中国人解放军三野之血吸虫防治工作时,曾立干部三等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据血防历史资料记载,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所辖的部队驻防上海西北郊,那里湖沼多,沟渠纵横。1949年夏秋之季,部队战士在水中锻炼身体,练习游泳,不料数天后大批战士出现发热、腹泻和腹胀等症状。更严重的是,据当时驻守在江、浙、沪血吸虫流行区的2个军、7个师的统计,在1949年至1950年间,战士的感染病例竟达33891人。
经上海医学界的专家教授认真分析,研究种种症状,最后确认湖水中隐藏着一种人的肉眼无法看见的寄生虫——血吸虫。上海医学院的流行病学专家苏德隆教授,紧急赶写了一份报告呈交宋时轮司令员,提出自己对防治血吸虫病的建议,得到上海市领导的高度重视。随后,由领导和专家组成的上海市血防领导机构迅速成立,上海各大医院、医学院组织1000余名医务工作者和学生奔赴沪郊部队驻地,为战士进行治疗。据记载,1950年1月至4月间共治愈1万多名战士。恢复健康的战士们,后来赴抗美援朝前线作战。在那次血防战役中,担任罗店分队分队长的刘约翰,立了三等功。
1952年2月,刘约翰又接到任务,任上海医学院血防大队大队长,到上海青浦县为农民进行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以前中国血吸虫病的肆虐情况。据记载,青浦县当时有30多万人口,患血吸虫病的就有15万人左右,感染率极高。如青浦县1951年应征兵役青年1328名,其中有血吸虫病的达97%。不光如此,在青浦,牛的感染率也达8.4%。而青浦县任屯村,是中国疫情流行的重灾区,病人“肚子像西瓜,脖子像丝瓜,手臂像黄瓜,脸色像菜瓜”。特别是肚子,无论男女,大得惊人。当时,社会上还广为流传着“只见死不见生,有女不嫁任屯村”的民谣。任屯村解放前全家死绝的有121户,死剩1人的28户,解放时全村人口仅剩461人,减少约1/2,其中患血吸虫病的97.3%。有人因此总结出血吸虫病有六害:害生命、害生长、害生活、害生育、害生产、害生趣。
上海医学院1957级的学生、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医学院成为刘约翰同事的马映雪,至今还记得读大学时在青浦县七宝镇参加血防工作的往事。
七宝镇历史悠久,因古寺七宝教寺得名。七宝教寺香火繁茂,人来人往,影响方圆百里。
从环境看,寺前有香花浜,右寺池浜转后接横沥港。香花浜上有3座桥,寺的四面都有水,且和蒲汇塘贯通。其实,正是因为附近农村水面多、沟渠多,使这里成了血吸虫病传染的高发之地。
马映雪回忆,上海医学院1957级的学生都被动员起来,下放到农村参加血吸虫病的预防和救治。学生一般两人一组,一人当医生,一人当护士,有时既当医生又当护士,吃住都在农民家里。苏德隆教授、钱惪教授是上海地区及学校的血防负责人,在一线具体指导的就是刘约华山医院任传染科副主任,还担任了传染寄生虫病教研室副主任,已具有相当水平的治疗经验与科研能力。
那时的刘约翰年轻,精力旺盛,几乎天天骑着脚踏车奔波于青浦县的农村,挨镇挨村地跑。他的日常工作,是与每一个血防小组见面,指导工作,沟通和交流情况。具体说,他一要查小组每天的工作记录,特别是病人大便的收集与寄生虫虫卵的化验情况和统计情况;二是要详细了解病人的治疗情况;三是要了解当地血防措施的落实情况。
收大便起初并不顺利,有的农民开始不理解也不愿意配合,特别是看见女同学上门,更是能推就推,能躲就躲。还有小孩子嘻嘻哈哈跟着起哄,叫他们“收屎医生”“验屎医生”。刘约翰和工作组成员耐心地做思想工作,进行科普教育,慢慢消除了一些“老顽固”的顾虑,从收大便到化验于是变得有条不紊,建立了良好的工作规范。
血吸虫病的治疗则具有更大的严峻性和挑战性。当时治疗的药物主要是锑剂。锑剂用于治疗血吸虫病始于1915年,在当时是治疗血吸虫病疗效最好的药品,几乎无可代替。可是它的毒性很大,缺点也比较突出。病人使用锑剂后常常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头晕及打寒战等症状,反应很多,严重者可能致死。孕妇血吸虫病患者使用锑剂后,则容易引发流产或早产。而且经锑剂治愈者仍有一定的复发率。在实际治疗中,锑剂一般采取静脉注射,稍有不慎,药水如漏在皮下,就可能发生红肿、剧痛及溃烂,心脏也难以承受,严重者会导致死亡。
因此,刘约翰带领工作组成员,对病人的年龄和病情等进行全面了解和分析,根据病人个体情况调整药物剂量,仔细观察和记录病人的不同反应。对危重患者还亲自加以特别监护,以尽量减少治疗过程的危险性。
在与血吸虫作战的过程中,查灭钉螺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南方地区的钉螺很多,而钉螺是血吸虫病的惟一中间宿主,它主要在河岸、河道、稻田等低洼潮湿地带生存与繁殖,而且繁殖很快。
苏德隆教授曾在1954年提出人尿消灭粪中血吸虫卵的方法,主要利用粪尿混合发酵时产生的氨来消灭虫卵。他还通过研究,判定最适于钉螺的温度是13℃,最适于钉螺的光线为晨曦和黄昏。他还发现砷酸钙和亚砷酸钙的灭螺作用,等等。这些研究不少都通过刘约翰与血防小组应用到实际中。
由于农民生病导致农村劳动力紧缺,血防小组成员还要参加当地灭螺的具体工作,如河岸清淤、河渠整治、挖土翻晒等。马映雪说,冬天,女生也参加挖河泥在太阳下翻晒,一人要挑60来斤土到河坡上。而且,这种方法灭螺还不是一蹴而就,几乎年年都挖都晒。
刘约翰与血防小组成员还动员农民们改变日常生活习惯,不直接饮用河里或者田里的水,不乱排乱倒大便,不在河边洗刷马桶等等。这些传统的生活习惯哪怕做一点点改变也非常困难,有的人改了又悄悄再犯(因为各种条件所限)。刘约翰等人与农村的基层组织及血防人员密切联系,一步一步地推进,一项一项地落实,对查灭钉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59年3月,已是副教授的刘约翰随钱惪教授等从上海医学院调到了重庆医学院,同时他们也把寄生虫防治以及血防工作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带到了四川省和重庆市(其时重庆属于四川省),并且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开辟血吸虫治疗新纪元
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血防工作一直是重要的主题。刘约翰的足迹,也深深地留在了四川的广汉、眉山、夹江、绵竹、大竹、安县等地。
1970年,张才全刚分配到重医附一院,就与刘约翰一起到眉山县太和区搞血防工作。四川的农民住房散居的多,搞血防必须走村串户。他记得,那时农村有很多狗,见了生人就绕前绕后地狂吠,作扑咬之状。年轻人拿着木棍走在前面,吆喝狗,刘约翰怕狗,也拿起木棍比划,紧跟着队伍。不过,一旦到了农家院子,哪怕左右有狗,他也毫不在乎,只顾盘问病人情况,观察变化,盯着病人把药喝下。
农村的院落四周都有树有竹,天黑时,什么也看不清。有一次大家摸黑回住地,刘约翰看不清路掉进了粪坑,等爬出来时全身都是粪水,狼狈极了。别看刘约翰学术精湛,生活能力就逊色多了。农村人洗衣服,多在田边和水井旁,刘约翰也拎着衣服去洗,在水里荡几荡、抖几抖,根本洗不干净。有时女同学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笑着主动帮老师洗。不过,只要搞科研,他就像换了一个人。
张才全说,“文革”期间,刘约翰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曾经“被改名”为刘跃——造反派当着喊他“流尿”(谐音)。那时,医学院的专家教授到农村去,一方面是血防工作确实离不了,另一方面是让他们去参加劳动,进行思想改造。不过刘约翰只要到了农村,从不懈怠,总是一面治疗一面搞科研。刘约翰等老一辈医疗工作者做事科学严谨、认真投入的精神,对张才全影响很大。曾经,张才全在水针麻醉的实验中自愿当实验对象,让医生用水针打自己的穴位。原来准备用井水,后来改用蒸馏水,打在皮下非常疼痛。他说,和刘约翰一样,这就是医生的奉献精神。
陈雅棠(曾任重庆市人大副主任),是中国高考恢复后刘约翰教授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1979年)与第一个博士研究生(1982年),他曾经在1980年代前期跟老师上山下乡搞血防。何谓上山?他介绍说,四川省内江以西的农村地区曾经血吸虫病流行,成都平原和山区都有。血吸虫的疫区有河网型、湖沼型和山丘型,流行的模式有所不同,而四川省的安县属于山丘型。
安县于1956年就发现钉螺和血吸虫病患者,是四川省血吸虫病重流行区之一。安县海拔高,交通不便,农民居住分散。在那里搞血防,艰难困苦可想而知,甚至要冒生命危险。20世纪80年代,刘约翰已60多岁了,仍然坚持在一线。
通常,一个村,如果出现一个病人或者几例病人,那么一个村的几百人都要做检查,一个不漏。检查,必须做到“三送三检”,即每人每天要送一次大便,连送3天,连检3天。农村缺劳动力,农民怕耽搁上工,还有生活习惯、生活顾忌等,有的人包括病人也不够配合,因此血防人员常常堵在农民家里收大便。晚上,没有电灯,刘约翰等医生经常打着手电筒在显微镜下查毛蚴或数毛蚴。陈雅棠说,让他尤其感动的是,从1950年搞血防到1980年代中后期,老一辈医疗工作者一做就是30多年,而且他听说刘约翰对有的血吸虫病人的随访工作也坚持了30多年。
不断的积累,不断的探索,使重医附一院血防团队在新药合成上取得了重大突破。1964年4月,重医附一院传染病教研室开展新药筛选工作,最终发现“血防846”(六氯对二甲苯)对动物血吸虫有显著疗效。这一发现,被业内评价为“是血吸虫病治疗史上划时代的创举,跳出了半个世纪沿用锑剂的框框,开辟了血吸虫治疗史上的新纪元”。
值得称道的是,继“血防846”之后,刘约翰团队又进行了“7505”与“7720”药物的临床及实验研究,并取得成功。1988年,刘约翰团队的学术成果《左旋吡喹酮的化学合成、药理与治疗日本血吸虫病的研究》,获得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一个好的医生永远在现场”
“发现苗头,走在前头”——这是刘约翰在传染病和寄生虫预防和治疗中的重要观念。他也经常对年轻医生强调“科研与现场结合”,认为传染病及寄生虫的发现与救治决不能离开“现场”。所以,每当发现疫情,刘约翰总是及时出现。
曾经,重庆610厂发生过一次影响较大的肺吸虫疫情。该厂前身之一是重庆裕丰纱厂,抗战时内迁到沙坪坝区土塆。后来因为国防保密需要改成重庆610厂,其中包括重棉一厂、重棉二厂、重庆印染厂和重庆红岩纺织配件厂,规模大,人数多。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有一年,该厂突然出现不少工人患病的情况。病人普遍症状表现为发热、咳嗽、盗汗、乏力及食欲减退等,有的人咳嗽痰带血丝,病情严重者,痰的颜色为铁锈色或褐色。重庆610厂医务室把病人当普通的感冒发烧来治疗,无论怎么用药,病症仍然反复,甚至可以说无济于事。工人与附近家属区人心惶惶,厂里只得求救于重医附一院。
刘约翰等医护人员紧急赶赴重庆610厂,对工人进行救治。通过种种医疗手段,特别是通过化验,发现患病工人身上都有同样的寄生虫,最后确认为肺吸虫。于是对每一个工人询问病史,到过哪里,吃过什么,喝过什么,终于搞清楚了寄生虫的来源。原来工人们曾经到潼南县(今潼南区)参加集体劳动,口渴之后喝了溪沟的水而感染了肺吸虫。问题找到后,对症下药,病人得到医治。
刘约翰等医生在重庆肝吸虫的发现与确认上也有很大贡献。有一年,刘约翰应邀到重庆外科医院会诊,对象是重庆钢铁公司的一名年轻工人,平常身体很棒,没有病症。这次发病,出现高烧、黄疸,经过两个星期治疗,高烧退去,黄疸不减,而且有加深现象。经检查,病人大便里有点白色,发现血液中白血球较高,等等。后来,这位病人转到重医附一院传染科进行治疗。刘约翰提醒医生,一定要注意在大便里寻找寄生虫,经过反复化验,最后找到了肝吸虫。
这是重医附一院发现和收治的第一例肝吸虫病人,属急性爆发性感染。经过反复询问得知,原来这个年轻人有一个怪癖,喜欢生吞小鱼,一次七八条,吞的时候,张开大嘴,将鱼头朝下,尾朝上一气吞下。这就是他得肝吸虫的原因。找到病源之后,刘约翰及时带领大家进行流行病调查,地点包括重钢地区附近的溪流和堰塘,还追踪到了万盛地区。刘约翰讲,搞传染病治疗和研究的人,一旦发现病源,必须追踪不舍,以避免大的疫情出现。
刘约翰到了晚年,将工作重点转入包虫病的治疗与研究。他曾经到甘孜州的石渠县治疗包虫病,也曾两赴新疆畜牧区,进行动物与环境比较的相关性考察。“一个好的医生永远在现场”,这句话正是刘约翰从医一生的真实写照。
2013年8月13日,刘约翰去世,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