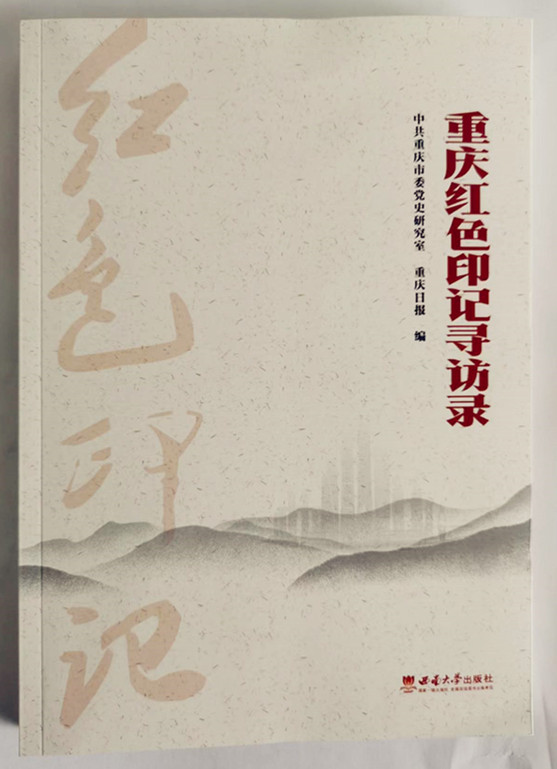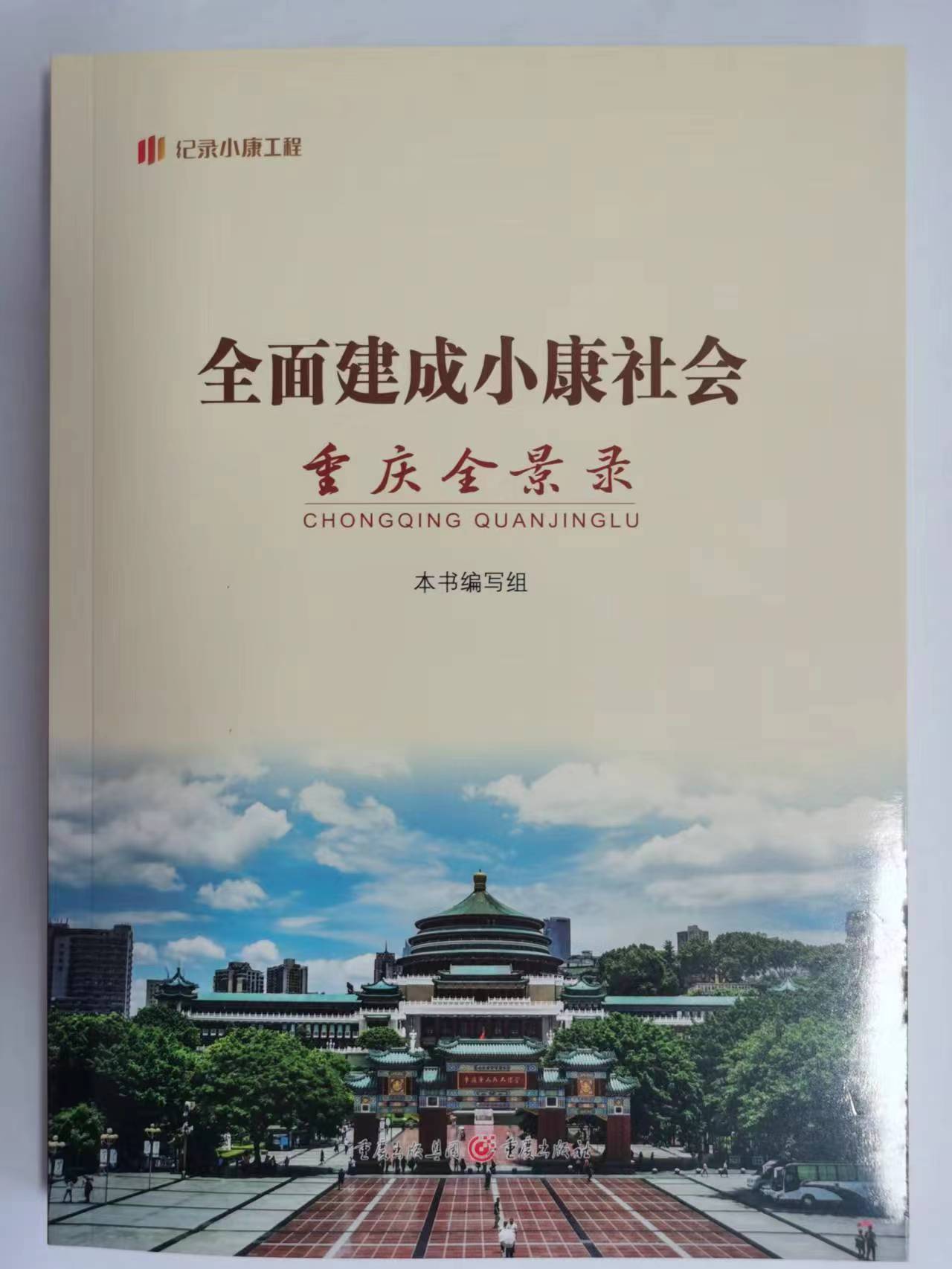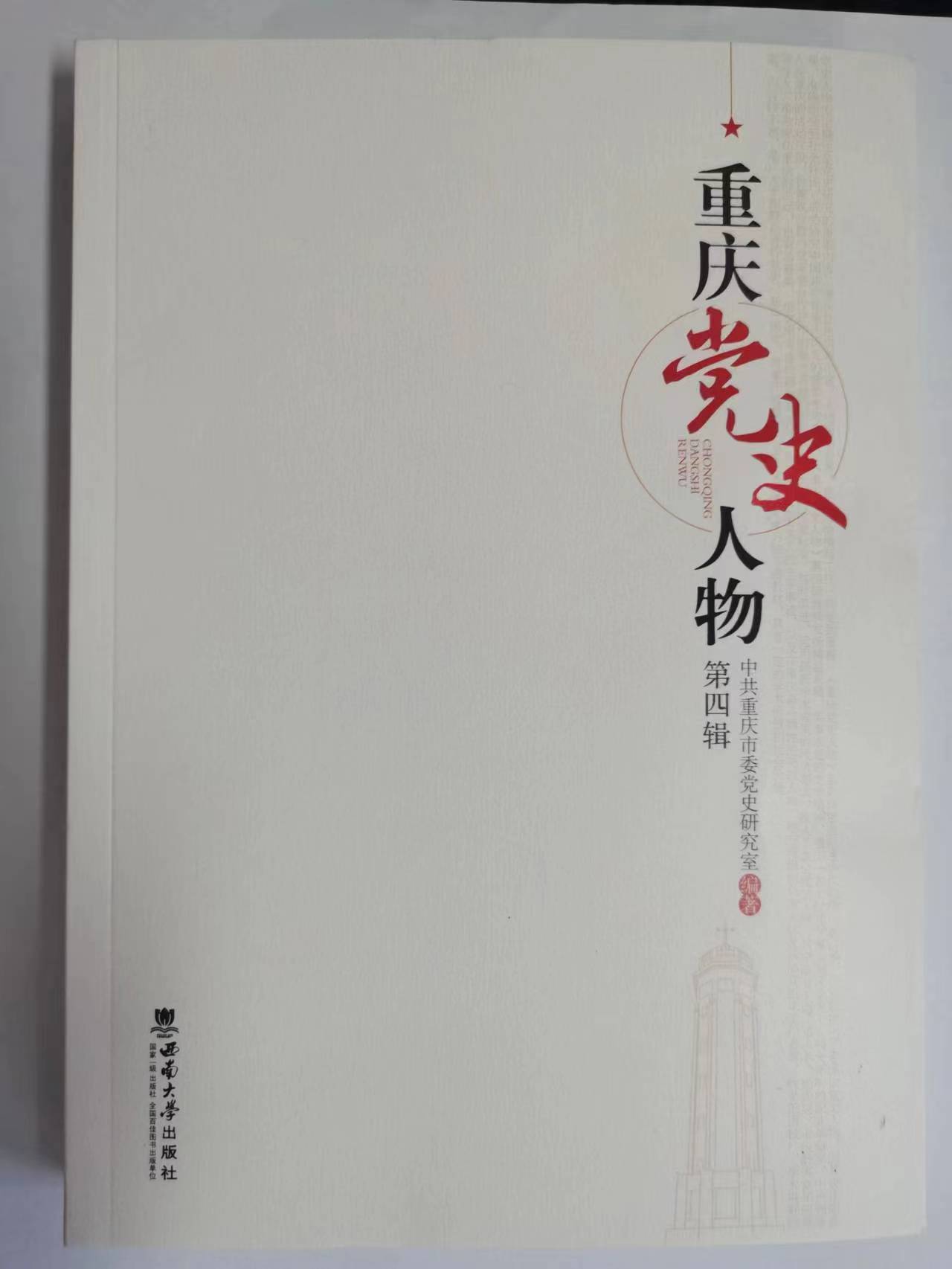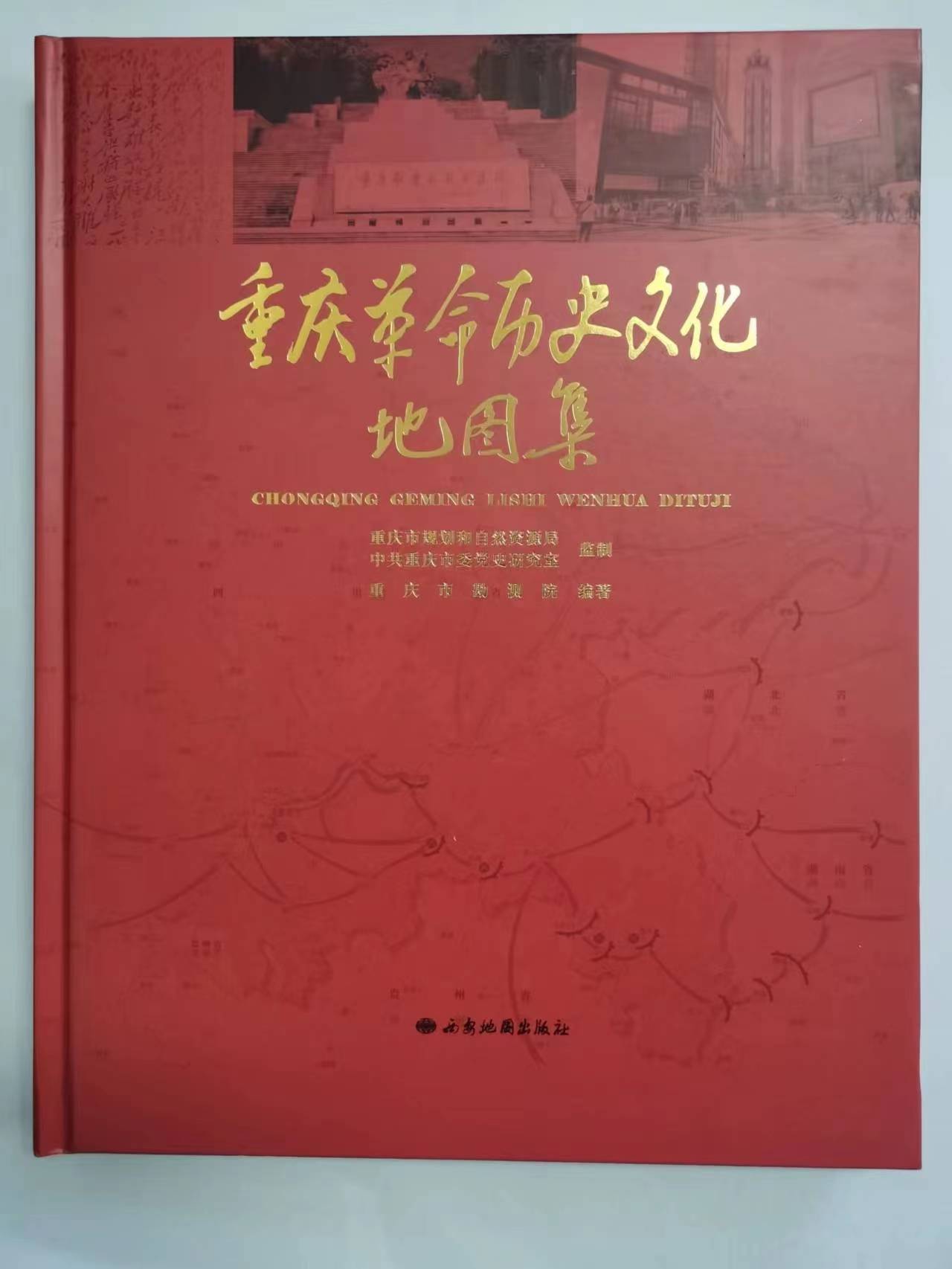唐润明
虽然蒋介石早在1935年就已决定将四川作为对日抗战的大后方、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据地。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首都究竟迁到什么地方,却一直悬而未决。直到是年11月12日蒋介石与林森晤面会商并共同决定迁都重庆之前,都没有国民政府究竟会将首都迁到某一具体地点的记载和说明。那么,重庆为什么能在四川乃至西南众多的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的不二选择呢?
笔者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除了重庆具有四川所包含的“地大、物博、人众以及深处内陆,不致遭敌人直接威胁”等优势外,重庆自身也具有几个方面的优势。
地理上处于“腹心”位置
重庆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西连三蜀,北通汉沔,南达滇黔,东接荆襄。在今天中国的版图内,重庆在地理上处于中国的“腹心”位置,距中国陆地的最东端、最西端分别为3186公里、3150公里,距中国陆地的最南端、最北端分别为2934公里、2925公里。因此,重庆既是中国西部与中部、东部的结合点,又是联结中国西部地区西南、西北的枢纽。这种“腹心”位置,既有利于沿海地区工厂、学校、机关、人员向重庆迁移和疏散,也有利于大后方各地兵员、物资等向前方运送。
在空间上,重庆与上海的直线距离为1450余公里,与南京的直线距离为1200余公里,与武汉的直线距离约756公里。而从川鄂接口——宜昌到重庆的实际距离,则为560公里。在此约560公里至1450余公里的空间范围内,除了一条长江以及少量的航线相连外,是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可通的。即使是长江,大型船只也只能航行到宜昌。宜昌以上至重庆段的川江,夏季洪峰时波涛汹涌,冬季枯水时暗礁凸现,被人们称为航运中的“绝地”,航行十分困难和危险。
更为重要的是,重庆以东到湖北宜昌,均为崇山峻岭,其北部、东部及南部分别有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大娄山环绕,地势特别险要,易守难攻。且无公路、铁路相接,仅有的长江水道,也是水急、弯多、滩险。在当时的条件下,日军要从地面攻到重庆,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所以蒋介石在1935年3月2日抵达重庆的当天,就有“不到夔门巫峡,不知川路之险也”的感慨。
数百上千公里的直线距离,使得重庆与战争、战区以及前线保持足够的战略纵深距离,从而保障首都的绝对安全。正如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山大学校长邹鲁1937年12月4日抵达重庆后,在回答记者“我们为什么要迁都重庆”这一问题时称:“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沿江沿海岸的防御武力,皆不及日本。因此,我们要求一个敌人的海军、陆军和空军都不能来的完善地方,作我们政府的根据地,这是中央政府迁渝主要原因。”
事实上,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决定将首都远迁数千里之外的重庆,应该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一个重大、正确的战略性决策。因为在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之后,无论是1940年5月至6月日军发动宜枣会战,西犯攻占宜昌,还是1944年4月至12月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南下攻占了作为重庆屏障的贵州独山、八寨,虽然都对重庆造成过一定的威胁,但日军地面部队始终未能进入四川,更没有到达重庆。
试想,如果当时国民政府不打算迁都重庆,接受了汪精卫关于“如须迁都,应以武汉或广州为宜”的建议,而武汉、广州在抗战爆发仅一年时间即告陷落,那么,此时的国民政府,要么屈服,要么再次迁都。因此,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1937年11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上关于“国民政府迁移是为战略决策,且只可迁移一次”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地势上构筑了天然防御屏障
在自然地理上,重庆坐落在四川盆地东南部、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居于川东南延行的平行岭谷与川中丘陵、川南山地的结合部,地势地形变化极大。不仅在重庆城区这一狭小的范围内是“山高路不平,出门就爬坡”“城在山中,山在城中”,而且近郊的江北(今重庆市渝北区)、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等地,因为地质及地势上的原因,也是关隘林立,群山环峙。
重庆有着绝好的天然防御屏障。清乾隆《巴县志》在描述重庆的军事地位时称:“渝州虽东川腹壤,而石城削天,字水盘郭。山则九十九峰,飞拴攒锁于缙云、佛图之间。内水则嘉陵、白水会羌、涪、宕渠来自秦,外水则岷、沫衣带会金沙来自滇,赤水来自黔。俱虹盘渝城下,遥牵吴楚、闽越、两粤之舟。昔人以地属必争,置重镇,间为制抚军驻节,良有以也。”又有“惟渝城汇三江,冲五路,鞭长四百三十余里,俯瞰夔门,声息瞬应。而西玉垒,北剑阁,南邛崃、牂牁,左挟右带,控驭便捷。故渝城能守,可俾锦官风雨,坐安和会矣”的记载。民间也有“天生的重庆铁打的泸州”之说。所有这些,都说明了重庆军事形势的险固和军事地位的重要。
不仅如此,重庆还是著名的山城,清末名臣张之洞曾这样吟咏重庆:“名城危踞层崖上,鹰瞵鹗视雄三巴。”张安弦也对重庆有“山作城墙岩作柱,水为锁匙峡为关”的描述。重庆地下,到处都是坚硬的岩石,对于建筑防空避难设施,是再好不过了。在此方面,蒋介石虽没有留下什么记载,但与蒋过往甚密、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则留下了自己对此的看法。
1935年5月下旬,罗家伦“为了商量冀察事变的问题”,同时表述自己有关“对日问题”的态度和看法,乘蒋介石专机自南京经重庆飞成都,向时在四川指挥“剿共”的蒋介石进行陈述和请示。
此次飞临重庆,罗家伦只是一个匆匆过客,仅呆了一天即飞赴成都。3天之后,罗家伦因急于赶回南京主持中央大学的毕业典礼,乘专机经重庆转飞南京,但因重庆遇大雾,天气不好,不能飞行。罗家伦一行只能滞留重庆,等待天气好转。在两天半时间里,罗家伦对重庆及其附近地区作了考察,从而加深了对重庆的认识和了解。后来,罗家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因为气候不好,我们在重庆耽搁了二天半,我就利用这段时间在重庆观察地点。因为我从汉口飞重庆的时候,观察过了宜昌以后山地的形势,便感觉到若是中日战事发生,重庆是一个可守的地点。回程到了重庆,我便存了一个心,为中央大学留意一块可以建设校址的地方。我亦了解在中日战争的过程中,空袭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重庆山势起伏,层岩叠障,易于防空,觉得这是一个战时设校的理想地点,像沙坪坝、老鹰岩,也是我游踪所到地方。可以说我这二天半在重庆的游览,赋给我对于重庆的形势一种亲切的认识。
罗家伦这样的文人,只在重庆待了两天半,就有这样的认识。那么,时为全国最高军事长官的蒋介石,1935年在重庆呆了数月之久,且足迹遍布重庆及其附近的浮图关、老鹰岩、江北、南岸和广阳坝等地,他对重庆在未来战争中重要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恐怕远在罗家伦之上。在蒋介石档案中,就曾于1935年3月7日留下了“甲、军事以利用天时、气候、地利、山河、道路与敌人阵势,以了战事。乙、须争先着,不争小利”的记载。
事实上,重庆城区到处是坚硬岩石以及周边的崇山峻岭,后来对战时首都重庆的防卫发挥过巨大作用。从1937年到1942年,重庆的防空避难设施从54个增加到1603个,其容量也从7208人增加到427673人。短短的6年间分别增加了29.69倍和59.32倍,为抗战时期重庆在遭受日机长时期、大规模、残酷野蛮的“无差别”轰炸下,保卫战时首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国民政府各院部会正常地行使职能,发挥过重大、积极和特殊的作用。
气候多雾避过日机全年轰炸
重庆位于北半球副热带内陆地区,气候温和,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其气候特征犹如民间俗谚所称:“春早气温不稳定,夏长酷热多伏旱,秋凉绵绵阴雨天,冬暖少雪云雾多。”温和的气候,不仅适宜人居住,也适宜粮食和蔬菜生长,所谓“四季宜农”是也。主要农作物有水稻、小麦、玉米、红薯、高粱等,经济作物则有油菜、花生、大豆。至于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一年四季都不曾断过。
重庆曾是有名的“雾都”,每年秋末至次年春初,大多处于浓雾之中,年平均有雾的日子多达近百天。每逢雾天,满城云缠雾绕,大街小巷缥缈迷离,数百米之外不见人影。著名作家张恨水在《重庆旅感录》一文中写道:凡游历四川者,虽是走马看花,但却有两点不可磨灭的印象,“其一为山,其二为雾”。他在描写重庆的“雾”时,这样写道:
就愚在川所经历,大抵国历十一月开始入雾瘴时期,至明年三月渐渐明朗。即明朗矣,亦阴雨时作,不能久晴,苟非久惯旅行,贸然入川,健康必难久持。其在雾罩时期,昼无日光,夜无星月,长作深灰色,不辨时刻。晨昏更多湿雾,云气弥漫,甚至数丈外混然无睹。
抗战时期,在日本陆军地面部队不能到达、只能靠空军进行远程轰炸时,这种浓雾对重庆形成了天然保护屏障,以至于在抗战时期日机对重庆所实施的长达5年半的野蛮轰炸中,每年只能在4月至9月间进行。而在当年10月至次年4月,则给重庆人民留下了一段休养生息、重建家园的空隙。
从抗战时期日机对重庆的轰炸情况来看,有数据统计,1939年从1月7日始至10月5日止(1 月)3次轰炸为试探性轰炸,大规模的轰炸从5月3日开始),1940年的轰炸从4月24日起至10月26日止(日军是年所制定的大规模轰炸重庆的“101号作战计划”,其预定的时限也是从4月到9月),1941年的轰炸从1月2日起至9月28日止(其中1月1次,3月1次,大规模的轰炸也是从5月开始的)。虽然日机狂轰滥炸,但几乎每年都能给重庆人民留下半年喘息的机会,这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是多么难得。
相信带兵打仗又颇重视防空的蒋介石,在考虑迁都这一重大问题时,对此也是有所虑及的。
水运交通优势发挥巨大作用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城区又恰恰位于长江、嘉陵江的汇合处,交通十分便利。
借助长江水运,重庆向东可直达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省市,并通联于世界各地,把长江中下游及沿海各地紧密地联系起来;向西又可通过长江、嘉陵江及其众多的支流,沟通与四川其他各地以及贵州、云南、陕南、甘南等地的联系。在四川境内,长江流经四川的长度虽达到2800公里,但其中心点和枢纽,则是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重庆。特别是长江的重要支流嘉陵江,总长800余公里,流域面积多达16.3万平方公里,而且通过嘉陵江的支流渠江、涪江,还连接了广大的川西北、陕南、甘南地区。
在近代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工具出现之前,四川以及整个西南地区的绝大部分物资运输,都是通过纵横交错的水路,源源不断地运到重庆,再由重庆运往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的货物,也以重庆为集散地,再通过水路纷纷转运到广大的四川及西南、西北各地。重庆不愧有“隐握长江上游之牛耳,西南诸省之锁钥”之谓。
重庆的这种交通优势,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铁路缺乏,公路、航空运输刚刚起步之际,显得特别重要,对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也不无影响。
当时内迁重庆的国民政府官员,除极少数乘飞机到达、极个别从陆路乘车辗转抵达重庆外,90%以上的人,都是通过长江水运,乘船抵达重庆的;内迁的机器、物资与设备,则几乎全部是通过长江水运到达重庆,然后再通过重庆分转各地。在内迁的机器设备中,“其中或有一件即重十余吨至二三十吨者”,这在当时的运输条件下,陆运、空运是根本不可能搬走的,但通过长江水运,却能将这些庞然大物,完整地运到重庆。而战时西南各地数百万的壮丁,大量的粮食,各种各样的军需品,以及以重庆为中心生产的枪炮及其弹药,也主要是通过长江运往前线战场。
对此,主持当时内迁运输事宜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于1943年写道:
对日作战以后,……那时自己正在南京帮助中央研究总动员计划草案的时候,告诉民生公司的人员:“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这个期望,公司实践了。四川需要赶运四个师,两个独立旅到前方,公司集中了所有的轮船,替他两个星期由重庆、万县赶运到宜昌。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的工厂撤退,民生公司的轮船即以镇江为接运的起点,协助撤退。接着又从南京起,撤退政府的人员和公物,学校的师生、仪器和图书。从芜湖起,撤退金陵兵工厂,从汉口起,撤退所有兵工厂及钢铁厂。第一期运12000吨,两个月间完成了。第二期运80000吨,分为两段,集中扬子江上游轮船,担任宜昌、重庆间一段,集中扬子江中下游轮船,担任汉口、宜昌间一段。这时除这80000吨以外,还有政府的全部,学校的大部,航空委员会航空器材的全部,民间工厂的大部,通通需要内迁,其总量又远在80000吨以上。大半年间,以扬子江中下游及海运轮船的全力,将所有一切人员和器材,集中到了宜昌。扬子江上游运输能力究嫌太小,汉口陷落后,还有30000以上待运的人员,90000吨以上待运的器材,在宜昌拥塞着。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遍街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因为争着抢运的关系,情形尤其紊乱,我恰飞到宜昌,看着各轮船公司从大门起,直到每一个办公室止,都塞满了交涉的人们,所有各公司办理运输的职员,都用全力办理交涉,没有时间去办运输了。管理运输的机关,责骂轮船公司,争运器材的人员,复相互责骂。我才商船舶运输司令部召集会议,呼请“停止交涉”,以便“办理运输”。因为扬子江上游还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较大轮船尚能航行,于是估计轮船40天的运输能力,请各机关据此分配吨位,各自选运主要器材,配合成套,先行起运,其余交由木船运输,或待40天后,另订计划运输。如来不及,或竞准备抛弃。至于何轮装运何机关器材,由我帮助分配。各机关完全表示同意。于是开始执行,效能提高,不止加倍。40天内,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出三分之二。原来南北两岸各码头遍地堆满器材,两个月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两岸萧条,仅有若干零碎废铁抛在地面了。一位朋友晏阳初君称这个撤退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其紧张或与“敦刻尔克”无多差异。
试想,在当时的历史件下,如果没有长江这个水上交通大通道,而是靠汽车或飞机,要将如此多的人员和物资运到远离南京数千里的重庆,是根本不可能的。可见重庆在交通运输上的优势与便利,也应是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实为多种历史因素综合的结果。
重庆于1891年开埠,是西部地区开埠最早的城市。到抗战爆发前夕,已发展成为整个西部地区城市人口最多且最具规模的近代城市,是四川乃至整个中国西部地区最大的工业、金融和商贸中心。除此之外,近代以来,重庆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军事战略地位,以及便利的交通、发达的商贸、兴盛的金融等,在民国时期一直是各路军阀争夺的焦点。素有“四川王”之称的刘湘,就是依托重庆的便利与富庶,打败各路军阀。但是,随着1935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参谋团”入川,国民党中央的各种势力开始渗入重庆并以重庆为据点,向四川及西南各省大肆拓展,致使刘湘对重庆的控制逐步削弱,国民党中央对重庆的控制则一步步加强。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在重庆正式成立,重庆、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各省的政治、经济、军事、人事等大权,均牢牢控制在其手中。特别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际,国民政府对川康军队的整理以及“川军国家化”的成功,大大减少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各种阻力,从而为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奠定了可靠的政治基础。
做战时首都,如果单就城市而言,可能当时中国的许多城市都具备条件或者超越重庆,但如果综合考察,则非重庆莫属。这就是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成为国民政府迁都惟一选择地的原因。